无错不成文:常识性错误笑话百出
“音乐家”何平如果不懂音乐,不懂交响乐,只要谨言慎行,尽量掩藏起露马脚的机会,原也无妨混迹于学界,弄个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教授当当;对于那些对学术一窍不通,对音乐一无所知的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理工科大学的外行领导来说,何平的学历,以及他动不动就夹一些外文单词的论著,还有他偶尔出国的游历,已足以把他当成一个学术霸主或乐坛牛人了。偏偏这位艺术学院院长不懂得艺术历史常识,这位“音乐理论家”不懂得音乐理论的基本常识,在《交响音乐欣赏》如此短小的“编著”中竟然频频出现常识性错误,一方面使得这本书连同上述知识性错误呈现出千疮百孔、令人难以卒读的惨淡之状,另一方面也使得“编著”者自己变成了连常识都不懂的奇葩“学者”。
有点音乐和文学常识的人都不会对《仲夏夜之梦》感到陌生,它是莎翁的名著,也是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杰作,而门德尔松的同题标题音乐正是为莎士比亚这部名剧创作的,德文题名Ein Sommernachtstraum,包括一首序曲(作品号21),以及后来为剧本所作的配乐(作品号61)。但像这种艺术史上的常识到了何平的“编著”中就变了,变成作曲家“有感而发”的作品,甚至变成了“单独位音乐诙谐的音乐会序曲”了:序曲发展的第四阶段,“序曲作为一种独立的标题性管弦乐曲单独出现。这就是单独为音乐会写的音乐会序曲……这时的序曲有了更多的音乐表现特质,因为它已不受剧情的闲置了。如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序曲,这是作曲家有感而发的作品,虽然后来被用于为话剧配乐,但是序曲在此之前就已经写好了。”[ 《交响音乐欣赏》,第21页。]将莎翁的剧作称为“话剧”,乃是以后来中国式的命名反扣到英语原剧身上,不仅显得不伦不类,而且同样犯了常识性的错误。门德尔松的曲作,包括序曲,明显为莎翁同名剧作所写,不知何平根据什么硬说是为音乐会而写的音乐会序曲,根据是他杜撰的“有感而发”?难道为剧作配的音乐就不是“有感而发”的创作吗?
交响音乐由意大利式序曲发展而来,这是常识,但如何发展的,就需要凭借超乎艺术史常识的学术把握力进行分析。何平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学术把握能力,故而在艺术史常识方面常犯错误。他确认交响音乐从意大利式序曲发展过来的时候,是“曼海姆乐派的斯塔米兹首先在意大利式序曲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快速度的第四乐章,这为交响曲的结构布局奠定了基础”。[ 《交响音乐欣赏》,第40页。]而常识告诉我们,意大利式序曲系主调风格音乐,由快板、慢板、快板三个段落组成。在向交响乐过渡的过程中,第三乐章常处理为稍快节奏的小步舞曲,曼海姆乐派的施塔密茨及其子卡尔·施塔赛茨,还有坎章比希等音乐家,致力于交响乐写作手法和管弦乐队演奏风格的创新,在带有小步舞曲的三个乐章的基础上,加上快速的终曲乐章,从而初步形成了交响曲四个乐章套曲的雏型。由此可见,将施塔米茨一个人算作序曲-交响曲转换中的唯一者有违艺术史常识,而将序曲-交响曲变衍的关键放在“第四乐章”(快板)的增加,同样不符合艺术史常识。意大利式序曲本来在最后乐章就是快板,它在向交响曲转换的过程中,引入稍快速的小步舞曲才是最为关键的处理环节。
何平二级教授虽然常识有限,但还常常不失时机地加以卖弄,以至于常常出现常识性的笑话。他其实不懂得乐器的基本常识,前述对古钢琴的理解就暴露出来了,但他仍不甘心,在谈到双簧管的时候,他竟然说“‘双簧管’是从Oboe直译过来的”。[ 《交响音乐欣赏》,第5页。]他显然不懂得“直译”是与“意译”相对应的一种翻译方法,双簧管正好与外文Oboe不构成“直译”关系,而是典型的意译的结果。Oboe这一词来自法语中的高(Haut)和木材(bois)的合成语“欧波瓦”(Hautbois),后为强调该词中的结尾元音的发声而形成了目前这个oboe名词。何平不是翻译家(幸好不是),他的外语可能仅仅限于吓吓外行的水平,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他懂得藏拙,懂得敬畏常识和知识,我们可能仍然当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音乐人。可惜,有人一当上二级教授就忘了“级”别,只剩下什么了?
也许,尽管何平主攻西方音乐,但以西方音乐艺术的常识要求这样的博士还是有些苛刻。那好,让我们看看他对中国音乐文化的理解吧,拜托,再有常识性的错误可就把脸丢到家了。然而很不幸,人家有的是脸,丢都丢不及。且看人家如何分析《海霞组曲》:“《海霞组曲》基本再现了电影的故事,表现了以海霞为代表的我国南海女民兵的精神气质。从组曲中,既可以感受到南海女民兵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又体会了电影故事的跌宕起伏。”[ 《交响音乐欣赏》,第18页。]能够“体会”电影故事的跌宕起伏,确实已经非同一般,乐曲还“基本”再现了电影的故事,用词也算很保留很谨慎了。然而,他根本没有好好看过这部电影,更不知道这部电影的原作小说《海岛女民兵》,当然也不会知道小说作者黎汝清,做梦也不会想到《海霞》所展示的海岛不在南海,而在浙江温州的洞头县,那里是祖国的东海。只要稍微负责任一点,翻翻电影和小说原著,就知道这样的地理常识实在是连常识都算不上。但我们这位二级教授就是要犯常识以下的错误,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吕其明先生创作的管弦乐曲《红旗颂》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乐曲,乐曲中融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东方红》、《国际歌》等经典歌曲的音乐成分,热情歌颂了无数先烈为无形红旗而战、而死的英雄壮举,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在五星红旗照耀下昂首阔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这同样是共和国音乐史上的常识。但何平在此书的“编著”中一定要将作曲家的写作情境锁定在天安门广场:“它描写了人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到五星红旗时不平静的心情。”[ 《交响音乐欣赏》,第9页。]此曲写于1965年,那一年的天安门广场并无突出的大典或震撼性的运动,一定要将作曲家以及表现内容与天安门广场拘泥在一起,不知是想别出心裁还是想故弄玄虚。超越常识的别出心裁是可笑的做秀,挑战常识的故弄玄虚是恶劣的卖弄。
“对音乐进行研究的人,无论抱有何种目的都需要对音乐作品是怎样结构起来的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知识和分析能力。”[ 杨儒怀:《音乐分析》,第166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可音乐理论家何平教授就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不知道一部杰出的艺术作品其灵感触发都可能有一定的契机,但这种契机绝不会构成作品的全部,因而,严肃的理论探索者绝对不应该将艺术灵感触发点夸大为艺术创作的全部动力,更不应将作品的艺术价值锁定在固有的功用目标上。这应该是艺术创作的理论常识。何平显然对这样的常识一无所知,他经常非常执拗地将伟大艺术的创作与特定场景甚至是特定功用绑定在一起。他认定交响乐的“第三种是标题性的交响组曲”,并强调“这是专门为音乐会写的组曲,它具有标题性,它既不来源于戏剧,也不来源于电影”。[ 《交响音乐欣赏》,第14页。]不知除了他还有谁做这样的硬性“规定”?标题性交响曲只能“专门为音乐会”创作?音乐家在没有音乐会的时候就不能“有感而发”地进行创作?而且,谁说标题性交响曲就不能与特定的戏剧、电影联系起来?“19世纪,浪漫乐派的作曲家常常从芭蕾、戏剧、歌剧以及文学作品中取材,写成标题性的交响组曲。如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组曲》(出自其舞剧《天鹅湖》),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出自其为话剧《培尔·金特》所作配乐)……”[ 《艺术百科知识博览》,王志艳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作为“大众读者”,我宁愿相信这样的常识,绝不相信何平这样的可怜的砖家。
然而砖家很执着,他坚持认为序曲的不同类型中,“第三个是专门为音乐会而写的音乐会序曲,如中国作曲家李焕之的《春节序曲》……它形成了自身独立的乐曲篇章”。[ 《交响音乐欣赏》,第24页。]《春节序曲》是《春节组曲》的第一乐章,它的确经常被抽出单独演奏。它是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李焕之基于延安时期的生活体验,在1950年代创作的一部作品,展现的是当年革命根据地春节时热烈欢庆的场面。它的旋律曲调雅俗共赏,加之其表现的主题是非常具有群众基础的传统节日,因而从它诞生之后,逐渐演变成“春节”音乐的“主旋律”。只有非常奇葩的思维才能得出此曲是“为音乐会而写的音乐会序曲”的结论。但即使这样还不够,任何不幸进入何平眼目中的乐曲都有可能被界定为“专门为音乐会而写”的。这回轮到刘铁山、茅沅的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此名曲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先由刘铁山有感于粤北瑶族同胞载歌载舞欢庆节日场面,以当地传统歌舞鼓乐为素材创作了《瑶族长鼓舞歌》,后由茅沅将该曲的部分主题改编为管弦乐,最终完成了这首中国管弦乐作品中的经典——《瑶族舞曲》。这样的创作过程与特定的音乐会并无关系,然而何平非常奇葩地断言:“中国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也是专门为音乐会创作的”。[ 《交响音乐欣赏》,第30页。]可怜的砖家,他不知道可用于音乐会演奏的乐曲,并不能被理解为或形容为“专门为音乐会创作的”。
音乐创作于其他艺术创作一样,遵循着“内容决定着形式,内容改造着旧有形式,同时内容也创造着新的形式这一千古不朽的艺术创造原则”[ 杨儒怀:《音乐分析》,第204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同样,艺术创作与作品的用途其实是两回事,可以用于音乐会演奏与为音乐会演奏而创作绝对是两回事情。这是一个懂得艺术的人应该知道的最起码的常识。然而对于可怜的音乐理论家和平来说,常识的要求还是高了一些。(转自学术批评网)
“音乐家”何平如果不懂音乐,不懂交响乐,只要谨言慎行,尽量掩藏起露马脚的机会,原也无妨混迹于学界,弄个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的教授当当;对于那些对学术一窍不通,对音乐一无所知的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一个理工科大学的外行领导来说,何平的学历,以及他动不动就夹一些外文单词的论著,还有他偶尔出国的游历,已足以把他当成一个学术霸主或乐坛牛人了。偏偏这位艺术学院院长不懂得艺术历史常识,这位“音乐理论家”不懂得音乐理论的基本常识,在《交响音乐欣赏》如此短小的“编著”中竟然频频出现常识性错误,一方面使得这本书连同上述知识性错误呈现出千疮百孔、令人难以卒读的惨淡之状,另一方面也使得“编著”者自己变成了连常识都不懂的奇葩“学者”。
有点音乐和文学常识的人都不会对《仲夏夜之梦》感到陌生,它是莎翁的名著,也是德国作曲家门德尔松的杰作,而门德尔松的同题标题音乐正是为莎士比亚这部名剧创作的,德文题名Ein Sommernachtstraum,包括一首序曲(作品号21),以及后来为剧本所作的配乐(作品号61)。但像这种艺术史上的常识到了何平的“编著”中就变了,变成作曲家“有感而发”的作品,甚至变成了“单独位音乐诙谐的音乐会序曲”了:序曲发展的第四阶段,“序曲作为一种独立的标题性管弦乐曲单独出现。这就是单独为音乐会写的音乐会序曲……这时的序曲有了更多的音乐表现特质,因为它已不受剧情的闲置了。如门德尔松的《仲夏夜之梦》序曲,这是作曲家有感而发的作品,虽然后来被用于为话剧配乐,但是序曲在此之前就已经写好了。”[ 《交响音乐欣赏》,第21页。]将莎翁的剧作称为“话剧”,乃是以后来中国式的命名反扣到英语原剧身上,不仅显得不伦不类,而且同样犯了常识性的错误。门德尔松的曲作,包括序曲,明显为莎翁同名剧作所写,不知何平根据什么硬说是为音乐会而写的音乐会序曲,根据是他杜撰的“有感而发”?难道为剧作配的音乐就不是“有感而发”的创作吗?
交响音乐由意大利式序曲发展而来,这是常识,但如何发展的,就需要凭借超乎艺术史常识的学术把握力进行分析。何平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学术把握能力,故而在艺术史常识方面常犯错误。他确认交响音乐从意大利式序曲发展过来的时候,是“曼海姆乐派的斯塔米兹首先在意大利式序曲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快速度的第四乐章,这为交响曲的结构布局奠定了基础”。[ 《交响音乐欣赏》,第40页。]而常识告诉我们,意大利式序曲系主调风格音乐,由快板、慢板、快板三个段落组成。在向交响乐过渡的过程中,第三乐章常处理为稍快节奏的小步舞曲,曼海姆乐派的施塔密茨及其子卡尔·施塔赛茨,还有坎章比希等音乐家,致力于交响乐写作手法和管弦乐队演奏风格的创新,在带有小步舞曲的三个乐章的基础上,加上快速的终曲乐章,从而初步形成了交响曲四个乐章套曲的雏型。由此可见,将施塔米茨一个人算作序曲-交响曲转换中的唯一者有违艺术史常识,而将序曲-交响曲变衍的关键放在“第四乐章”(快板)的增加,同样不符合艺术史常识。意大利式序曲本来在最后乐章就是快板,它在向交响曲转换的过程中,引入稍快速的小步舞曲才是最为关键的处理环节。
何平二级教授虽然常识有限,但还常常不失时机地加以卖弄,以至于常常出现常识性的笑话。他其实不懂得乐器的基本常识,前述对古钢琴的理解就暴露出来了,但他仍不甘心,在谈到双簧管的时候,他竟然说“‘双簧管’是从Oboe直译过来的”。[ 《交响音乐欣赏》,第5页。]他显然不懂得“直译”是与“意译”相对应的一种翻译方法,双簧管正好与外文Oboe不构成“直译”关系,而是典型的意译的结果。Oboe这一词来自法语中的高(Haut)和木材(bois)的合成语“欧波瓦”(Hautbois),后为强调该词中的结尾元音的发声而形成了目前这个oboe名词。何平不是翻译家(幸好不是),他的外语可能仅仅限于吓吓外行的水平,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如果他懂得藏拙,懂得敬畏常识和知识,我们可能仍然当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音乐人。可惜,有人一当上二级教授就忘了“级”别,只剩下什么了?
也许,尽管何平主攻西方音乐,但以西方音乐艺术的常识要求这样的博士还是有些苛刻。那好,让我们看看他对中国音乐文化的理解吧,拜托,再有常识性的错误可就把脸丢到家了。然而很不幸,人家有的是脸,丢都丢不及。且看人家如何分析《海霞组曲》:“《海霞组曲》基本再现了电影的故事,表现了以海霞为代表的我国南海女民兵的精神气质。从组曲中,既可以感受到南海女民兵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又体会了电影故事的跌宕起伏。”[ 《交响音乐欣赏》,第18页。]能够“体会”电影故事的跌宕起伏,确实已经非同一般,乐曲还“基本”再现了电影的故事,用词也算很保留很谨慎了。然而,他根本没有好好看过这部电影,更不知道这部电影的原作小说《海岛女民兵》,当然也不会知道小说作者黎汝清,做梦也不会想到《海霞》所展示的海岛不在南海,而在浙江温州的洞头县,那里是祖国的东海。只要稍微负责任一点,翻翻电影和小说原著,就知道这样的地理常识实在是连常识都算不上。但我们这位二级教授就是要犯常识以下的错误,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吕其明先生创作的管弦乐曲《红旗颂》是一首脍炙人口的乐曲,乐曲中融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东方红》、《国际歌》等经典歌曲的音乐成分,热情歌颂了无数先烈为无形红旗而战、而死的英雄壮举,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在五星红旗照耀下昂首阔步走向社会主义的豪迈气概,这同样是共和国音乐史上的常识。但何平在此书的“编著”中一定要将作曲家的写作情境锁定在天安门广场:“它描写了人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到五星红旗时不平静的心情。”[ 《交响音乐欣赏》,第9页。]此曲写于1965年,那一年的天安门广场并无突出的大典或震撼性的运动,一定要将作曲家以及表现内容与天安门广场拘泥在一起,不知是想别出心裁还是想故弄玄虚。超越常识的别出心裁是可笑的做秀,挑战常识的故弄玄虚是恶劣的卖弄。
“对音乐进行研究的人,无论抱有何种目的都需要对音乐作品是怎样结构起来的这个问题有一定的知识和分析能力。”[ 杨儒怀:《音乐分析》,第166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可音乐理论家何平教授就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不知道一部杰出的艺术作品其灵感触发都可能有一定的契机,但这种契机绝不会构成作品的全部,因而,严肃的理论探索者绝对不应该将艺术灵感触发点夸大为艺术创作的全部动力,更不应将作品的艺术价值锁定在固有的功用目标上。这应该是艺术创作的理论常识。何平显然对这样的常识一无所知,他经常非常执拗地将伟大艺术的创作与特定场景甚至是特定功用绑定在一起。他认定交响乐的“第三种是标题性的交响组曲”,并强调“这是专门为音乐会写的组曲,它具有标题性,它既不来源于戏剧,也不来源于电影”。[ 《交响音乐欣赏》,第14页。]不知除了他还有谁做这样的硬性“规定”?标题性交响曲只能“专门为音乐会”创作?音乐家在没有音乐会的时候就不能“有感而发”地进行创作?而且,谁说标题性交响曲就不能与特定的戏剧、电影联系起来?“19世纪,浪漫乐派的作曲家常常从芭蕾、戏剧、歌剧以及文学作品中取材,写成标题性的交响组曲。如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组曲》(出自其舞剧《天鹅湖》),格里格的《培尔·金特组曲》(出自其为话剧《培尔·金特》所作配乐)……”[ 《艺术百科知识博览》,王志艳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作为“大众读者”,我宁愿相信这样的常识,绝不相信何平这样的可怜的砖家。
然而砖家很执着,他坚持认为序曲的不同类型中,“第三个是专门为音乐会而写的音乐会序曲,如中国作曲家李焕之的《春节序曲》……它形成了自身独立的乐曲篇章”。[ 《交响音乐欣赏》,第24页。]《春节序曲》是《春节组曲》的第一乐章,它的确经常被抽出单独演奏。它是我国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李焕之基于延安时期的生活体验,在1950年代创作的一部作品,展现的是当年革命根据地春节时热烈欢庆的场面。它的旋律曲调雅俗共赏,加之其表现的主题是非常具有群众基础的传统节日,因而从它诞生之后,逐渐演变成“春节”音乐的“主旋律”。只有非常奇葩的思维才能得出此曲是“为音乐会而写的音乐会序曲”的结论。但即使这样还不够,任何不幸进入何平眼目中的乐曲都有可能被界定为“专门为音乐会而写”的。这回轮到刘铁山、茅沅的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此名曲的产生过程是这样的:先由刘铁山有感于粤北瑶族同胞载歌载舞欢庆节日场面,以当地传统歌舞鼓乐为素材创作了《瑶族长鼓舞歌》,后由茅沅将该曲的部分主题改编为管弦乐,最终完成了这首中国管弦乐作品中的经典——《瑶族舞曲》。这样的创作过程与特定的音乐会并无关系,然而何平非常奇葩地断言:“中国管弦乐作品《瑶族舞曲》也是专门为音乐会创作的”。[ 《交响音乐欣赏》,第30页。]可怜的砖家,他不知道可用于音乐会演奏的乐曲,并不能被理解为或形容为“专门为音乐会创作的”。
音乐创作于其他艺术创作一样,遵循着“内容决定着形式,内容改造着旧有形式,同时内容也创造着新的形式这一千古不朽的艺术创造原则”[ 杨儒怀:《音乐分析》,第204页,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同样,艺术创作与作品的用途其实是两回事,可以用于音乐会演奏与为音乐会演奏而创作绝对是两回事情。这是一个懂得艺术的人应该知道的最起码的常识。然而对于可怜的音乐理论家和平来说,常识的要求还是高了一些。(转自学术批评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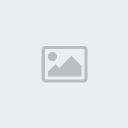
 首页
首页